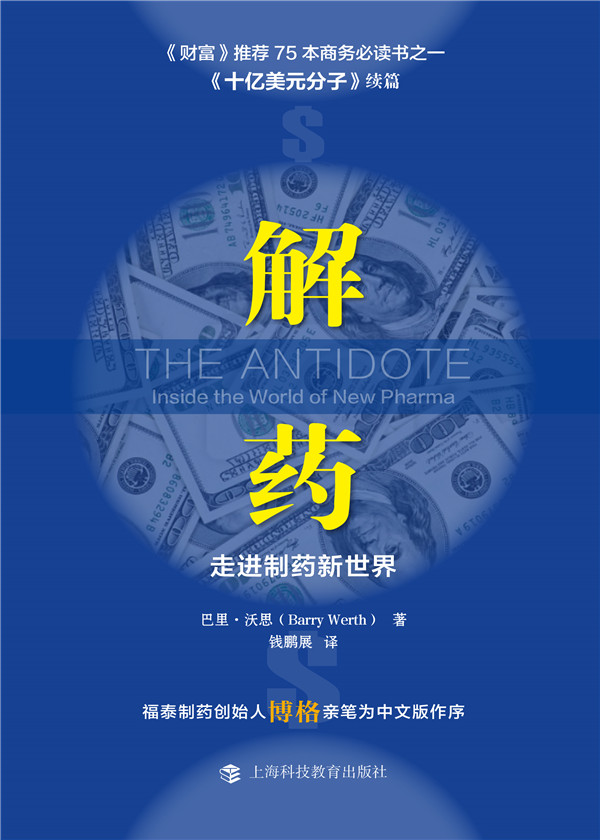
创造重要新药无疑是人类最复杂、最冒险也最不可能的挑战。想想看,口服或者注射外来物质,干预人类的疾病进程,这种想法是多么离经叛道,它无疑是人类认知的一次巨大跃进!而研发新药往往需要成百上千人二三十年的协作,本身就堪称奇迹。
与研发新药相比,将人类送上火星,并建立永久的殖民地,是一件几乎肯定能成的事:仅需要意志、金钱与能工巧匠。只要有这些资源,火星殖民地指日可待。我们已经知道关键步骤的要诀了,没有理由认为这事做不成。类似地,安全可控的核聚变发电技术——长期来看这是最可能普及的绿色能源——也必将实现。毕竟太阳上每分每秒都在发生核聚变,只需要弄明白如何在地球上实现它就成了。我相信,30年内,我们就能在这两方面取得进展。
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每一种疾病(比如阿尔茨海默病)都必然有“解药”。至少我们还不清楚,阿尔茨海默病的“解药”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在实验室模拟人类需要一生才能发展出的疾病?实验室模型一般是为了在短期得到结果,因此很难模拟那些日积月累的微小变化。在临床上,应该什么时候开始治疗疾病?症状出现时,是不是已经有不可逆转的损伤了?调节人体哪些生化途径才能延缓病程,这样做会不会引起难以预料的不良反应?我们总是(没有证据地)假设一定存在一种解药。但如果需要两种药物才能治疗疾病,且每一种药物单独作用都不够强,我们如何才能发现这种组合?或许有效的“解药”要在症状出现之前很久就开始用于治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何时该对何人进行治疗?如何开展耗时数十年的临床试验?这可能无法做到。
直到真的被做到。
药物开发的真正故事鲜为人知,因为这个过程跨越了漫长的时光,涉及了太多人。好莱坞对“秘密配方”诞生传奇的描绘一般是,一位孤独的科学家,在昏暗且与世隔绝的实验室中,灵光一闪,然后发现。你可以说这是马后炮般的简化,或者说是瞎扯淡。真正的故事涉及一群人,或者几群人,他们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享受集体创造中理想主义的喜悦,热情拥抱对复杂体系的科学研究。这些有幸参与的科学家成就了他们任何个人都无法独自实现的壮举。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不朽了:每一款重要新药都永久性地造福了人类。
有些愤世嫉俗的人会认为研发新药的动机“全是为了钱”,但至少这不是我的感受。对于那些乘机进来捞一笔就跑的人来说,或许的确如此。但对于核心研发团队而言,他们花费20年的时间,死咬一件事,如果只是为了最后赚点钱,那么这实在是最蠢的致富路线。明明有更轻松便捷的生财之道,比如搞个可供消磨时间的手机软件,或者当网红。参与新药研发绝对不适合那些没定力的人。
新药被“研究”与“开发”之后,还有一个不可或缺、充满创意的环节鲜少被谈及。重要新药不光能提供客观的数据,更应该改变看待疾病的视角、治疗疾病的方法、医务人员的预期,以及最重要的——患者的预期。重要新药应该能重新定义疾病,改变疾病对人类的影响,甚至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但药物本身只是药物,无论药效如何,都不能自动做到这些。在新药上市前后,让这些改变得以发生的活动一般被称为“市场营销”,这与大众认知中的“卖药”有很大不同。“销售”一款突破性药物,可以说是一家创新公司承担起将正确的药物送到正确患者手中的重任——没有销售创新的新药创新是不完整的。
基于以上原因,不难理解为何只有极少的新药研发被完整地记录,毕竟寻找新药、开发新药、上市新药的旅途动辄跨越20年,涉及数百人,不能奢望这一切能由一位中立客观的观察者及时记录。但是,巴里·沃思在《解药》及其前篇《十亿美元分子》中做到了。
如果新药是奇迹,那么志在不断开发出新药的公司则更为不可能。重要新药很少是一次性开发成功的。能开发出重要新药的公司总会同时开展多项有前景的项目,其间须承担巨大的不确定性,平衡资源,竭尽全力。平衡资源可不是单纯的会计行为,这将改变数百人的研究方向、职业生涯以及他们的一生。管理包括研究、开发及商业项目的资产组合,不仅靠分析,更需要直觉;不仅是制订计划或依照计划行事,更须持之以恒地追求科学价值和人类价值。开发新药更是创造一种独特的科研环境:招揽热情专注的人才,组建项目团队,形成接受甚至享受不确定性的科研文化。
这种环境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新药开发需要对“造福患者”这个共同目标持续投入,并尽可能无视沿途各种蝇头小利(比如个人职业生涯或者公司短期收益)的干扰。最后,当你拿出一款重要而成功的新药时,几乎所有的贡献者,不论从个人层面还是职业层面,都会获益颇丰。但是,通向成功之路需要专注、灵活、技巧……并坚持数十年。
当然运气也很重要。允许好运来临是新药开发的关键。运气或许不是必需的——如果你有无限的时间和资源。有句正确的废话是“如果你有无限的钱,你就能打败蒙特卡罗的赌场”。不管是在赌场还是在实验室,这在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要想“击败概率”,我们先要“下注”尽可能多的研究和开发项目。不过每个项目成功的概率着实很低,成功将药物送到患者手中的概率在1/30到1/100之间(取决于你怎么定义“成功”),有多个项目也不能保证成功。哪怕是最大的药企也不可能有这么多项目。既然建立多个项目不能保证“击败概率”,如何才能成功呢?
建立多个项目并不能确保成功,但能提高“好运气”的概率,也就是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对药物研发这个高度理性、讲究科学、充满高精尖技术的行业而言最为讽刺的是,我们其实最依赖不理性的运气。创造允许好运发生,并能识别、利用这些好运的环境和文化,就是不断击败概率的方法,就是成功的关键。
想要正确并不断地开发重要新药(虽然很少有人能做到),还需要夸张地相信并尊重个体的热情与集体的力量。价值观与环境的配合能吸引有助于成就这般野心的人才:他们都对自己以及团队非常有信心。我们不能指望好运在需要时出现,但是,允许好运发生并发现这些机会的文化是可以培养的。这样的文化接纳有热情的人才,允许他们失败并依然支持他们,能在意外的时机带来巨大的惊喜。
这些就是《十亿美元分子》以及《解药》的主旨。在福泰的早期,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福泰进行的与其说是科学和技术的实验,倒不如说是社会实验。技术、技巧以及思路都是新药研发的关键试剂,但是成功与失败的分界往往是能否形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能孕育愿意融入集体并在其中积极作出贡献的个体,充满这样个体的团体终能挑战不可能。
现实总是混乱的,故事总是回顾性的,只有部分的复杂现实能够被讲述。《解药》及其前篇的故事性是无与伦比的,但就像大部分的故事,为了让故事成为故事,难免简化了现实,强调个别人的成就。在每个被仔细刻画的人物背后,都有10个或者更多未被描述的人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过请理解,这不是本书的缺陷,这是所有故事的局限性,所以解读不能太片面。本书没有描述许多枯燥而无法逃避的琐碎工作,也没有那些我们都读腻了的没有结果的工作。
相反,本书讲述了在一家超越个体的企业中,穿行于恐惧与乐趣间的精彩旅程。“恐惧与乐趣”是一次为期数日的公司年度活动的标题。公司上上下下,不论是实验室的科学家,还是仓库的搬运工,都来进行海报展示,讲述这一年激动人心的事。新来的人往往不理解这个活动的意义。他们都很喜欢“乐趣”但是害怕“恐惧”。我们想表达的是,伴随“恐惧”的是强烈的乐趣,这是只有在赌注够大,大到有个人风险,大到可能一败涂地时才能体会到的乐趣。我们不害怕努力、不害怕失败,我们真正害怕的是平庸。没有恐惧的乐趣就像是在迪士尼乐园乘坐假独木舟在人造水渠中玩“激流勇进”,而不是在真正的湍流中跌宕起伏。迪士尼乐园“有趣”的游戏没有任何风险可言,感官刺激是刻意的,线路是一样的,结果是固定的,那是给孩子们的。在真正的“激流勇进”中,你希望并祈祷结果是好的,但是你需要为之努力。人的主观参与让真正的激流漂流有趣多了。
我很荣幸能够参与本书描述的不可能的漂流。我们自然是幸运的,旅程也是绝对有趣的。
乔舒亚·博格
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2022年2月9日
(本文经博格本人授权发表)
主要人物简介
括号内年份为人物在福泰任职时期。原书于2014年出版,人物职务可能有变动。
约翰·阿拉姆 福泰医学发展执行副总裁,首席医学官(1997—2006)。
马修·埃门斯 福泰总裁,CEO,董事会主席(2005—2012)。
理查德·奥德里奇 福泰资深副总裁,首席商务官(1989—2000)。
埃里克·奥尔森 福泰副总裁,囊性纤维化项目领导(2001—2013)。
鲍勃·比尔 囊性纤维化基金会CEO与总裁。
杰弗里·波格斯 投资银行伯恩斯坦的生物技术资深分析师。
肯·博格 福泰法务总顾问(2001—2011),乔舒亚·博格的哥哥。
乔舒亚·博格 福泰创始人,曾任 CEO(1992—2009)与董事会主席(1997—2006),董事(1989—2017)。
罗杰·邓 福泰药物研发副总裁(1989—2004)。
弗雷德·范古尔 福泰囊性纤维化项目生物学主管(2001— )。
拉斯·弗莱舍 FDA抗病毒部门资深临床分析师,替拉瑞韦(商品名Incivek)的主审评官。
翠西·赫特 福泰药剂开发资深副总裁(2004— )。
南希·怀森斯基 福泰销售总监(2009—2011)。
宾克·加里森 福泰资深副总裁,“催化剂”,主持福泰的价值观与愿景项目(2004—2009)。
约翰·康登 福泰制药生产与运营资深副总裁(2005— )。
罗伯特·考夫曼 福泰首席医学官,资深副总裁(1997— )。
亚当·科佩尔 溪畔资本执行董事,福泰重要投资人。
邝达仪 福泰副总裁,主管丙型肝炎药物开发(1997—2012)。
亚历山大·昆博 福泰销售副总裁,替拉瑞韦销售团队领队(2010—2012)。
杰弗里·莱登 福泰总裁,董事会主席,现任CEO(2012— )。
约翰·麦克哈奇森 替拉瑞韦的外部临床研究者,后任吉利德肝病治疗资深副总裁。
彼得·米勒 福泰首席科学家,全球研发执行副总裁(2002— )。
马克·慕克 福泰首席技术官,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1990—2011)。
保罗·内古列斯库 福泰科研副总裁,圣迭戈分部主管(2001— )。
迈克尔·帕特里奇 福泰投资者关系副总裁(1997— )。
阿米特·萨奇戴夫 福泰资深副总裁,主管全球政府策略、市场渠道与价值(2007— )。
维姬·萨托 福泰总裁(1992—2005)。
查尔斯·桑德斯 福泰董事会主席(1996—2010)。
伊恩·史密斯 福泰执行副总裁,首席财务官(2001— )。
约翰·汤姆森 福泰研发网络策略副总裁(1989— )。
杰克·威特 福泰药物注册副总裁(2009—2011)。
基思·约翰逊 囊性纤维化患者,参与Kalydeco的临床试验。
中文版序/ Ⅰ
主要人物简介/ Ⅶ
福泰的主要分子与药物/ Ⅸ
临床试验分期概念简介/ Ⅺ
引言我为什么重返福泰/ 1
第一部分饲喂巨兽/ 11
第二部分挑灯夜战/ 101
第三部分好戏上场/ 217
后记/ 351
致谢/ 355
文献与资料/ 358
附录1:年表/ 372
附录2:人名译名对照表/ 380
译后记/ 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