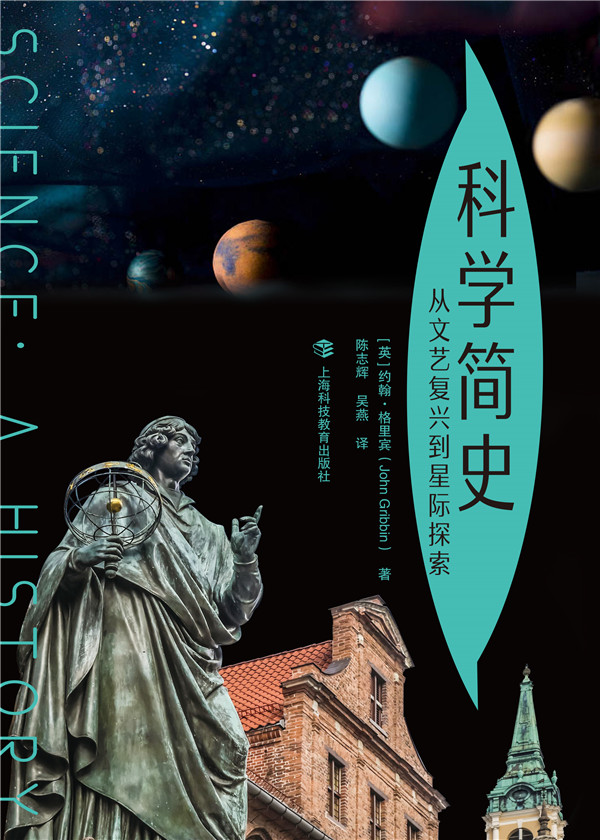
从文艺复兴至20世纪末,科学从自然哲学中蜕变,发展成为一幅由多个学科分支绘就的壮丽画卷。其中包括:牛顿经典力学,近代早期的博物学,启蒙时代的化学和经典热力学,19世纪的地质学、进化论、原子理论和经典电磁学,现代量子理论、遗传学,以及现代宇宙理论等多个领域。对于这些现在已成为中学和大学基本学习内容的科学知识,本书并未机械地堆砌起它们各自的历史,而是把握住技术与科学理论相互促进这一脉络,将其如何环环相扣、渐进发展的历史娓娓道来。对于那些大科学家,本书也多有信而有征又色彩斑斓的深入细致描写。这是一部西方科学的历史,也是写就这一历史的科学家们的个人史。
作者简介
约翰·格里宾(John Gribbin),英国著名科学读物专业作家,英国科学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得主,毕业于剑桥大学,获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职于《自然》(Nature)杂志和《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周刊。他著有百余部科普和科幻作品,内容涉及物理学、宇宙起源、人类起源、气候变化、科学家传记,并获得诸多奖项。《旁观者》(Spectator)杂志称他为“最优秀、最多产的科普作家之一”。他的科学三部曲《薛定谔猫探秘——量子物理学与实在》(In Search of Schr?dinger??s Cat: Quantum Physics and Reality)、《双螺旋探秘——量子物理学与生命》(In Search of the Double Helix: Quantum Physics and Life)和《大爆炸探秘——量子物理学与宇宙学》(In Search of the Big Bang: Quantum Physics and Cosmology)尤为脍炙人口,其余作品如《大众科学指南——宇宙、生命与万物》(Almost Everyone??s Guide to Science: The Universe, Life and Everything)、《创世138亿年——宇宙的年龄与万物之理》(13.8:The Quest to Find the True Age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Richard Feynman: A Life in Science)、《量子、猫与罗曼史——薛定谔传》(Erwin Schr?dinger and the Quantum Revolution)也广受好评。
致谢
我要感谢下列机构让我得以使用其图书馆及资料:巴黎的法国科学院与植物园;牛津大学图书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与自然历史博物馆;剑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伦敦的地质学会;肯特郡的达尔文故居;伦敦的林奈学会;皇家天文学会;皇家地理学会;皇家科学研究所;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剑桥大学图书馆。一如既往地,萨塞克斯大学为我提供了工作之所与支持,包括互联网接入。在与我讨论过此书各个方面的诸多人士中,无论单独提到谁都是不公正的,但他们都各自心中有数,而且所有人都应得到我的感谢。
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形式都在本书中出现。“我”,当然用在表达我本人对所呈现的科学问题的见解;“我们”则用在我的写作搭档玛丽·格里宾(Mary Gribbin)也参与撰写的时候。她在确保让本书文字令非专业读者读来也明白易懂方面给予的帮助对本书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正像在我所有的书里一样。
导言
关于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科学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一过程伴随着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工作而开始,并因伽利略(Galileo Galilei)而势头大增:16世纪,哥白尼的工作暗示了地球并不位于宇宙的中心,而伽利略在17世纪初利用一架望远镜获得的至关重要的证据表明,地球实际上是绕日运行的一颗行星。在随后几个世纪连续不断的天文发现热潮中,天文学家们发现,正如地球是一颗普通的行星一样,太阳只是一颗普通的恒星(银河系中数千亿计恒星中的一员),而银河系本身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星系(可见宇宙中的无数星系之一)。20世纪末,他们甚至认为,宇宙可能也不是唯一的。
与此同时,生物学家试图找到将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区分开来的特殊“生命力”存在的某种证据,但是失败了,从而推断出生命不过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化学形式。一种历史学家乐见的巧合是,人体的生物学研究开创之初的里程碑事件之一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的《人体的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于1543年出版,那正是哥白尼最终出版《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的同一年。这个巧合使1543年成为一个信手可得的标志性年份,标示出科学革命的开端,这一革命此后将首先改变欧洲,随后则改变了世界。
当然,无论选择哪一天作为科学之历史的开创之日都是随意的,而我自己的考虑则受制于地域因素以及它的时间跨度。我的目标是勾勒出西方科学从文艺复兴至(大约)20世纪末的发展。这意味着要把古希腊、中国以及伊斯兰科学家与哲学家的成就暂且放在一边,在欧洲被称为黑暗时期和中世纪的年代,他们仍孜孜不倦、始终如一地探索着有关我们宇宙的知识。这还意味着讲述一个条理分明的故事,它关乎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这是我们对于宇宙以及我们如今在其中所处位置的理解的核心,而这个故事在地点与时间上都有着明确的起点。因为人类生命被证实与地球上其他任何生命并无二致。正如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华莱士(Alfred Wallace)在19世纪所建立的学说,人类与变形虫之间的区别仅在于经由自然选择的进化历程以及大量的时间。
我在这里提到的所有例子还突出了另一个叙事特点。根据在科学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个人,如哥白尼、维萨里、达尔文、华莱士及其他人物的工作来记述关键性事件,这是很自然的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是作为一系列无法替代的天才人物的工作成果而发展进步的,这些天才对宇宙的运行方式拥有一种特殊的洞察力。这些人物也许是天才(尽管并不总是),但肯定不是无法替代的。科学的进展是一步步推进的,而且正如达尔文和华莱士的事例所显示的,当时机成熟之际,两个或更多人可能会各自独立地向前推进。谁会作为一种新现象的发现者而名留青史,这是中彩票般的运气或历史的偶然。远比人类天赋重要得多的是技术的发展,所以并不令人惊讶的是,科学革命的开始是与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展同时发生的。
我只能想到一部分例外的情况,即便如此我还是会比大多数科学史家描述更多的例外情况。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显然是某种特殊的情况,这不仅因为他的科学成就的范围之广,还因为他以一种清晰的方式确立了科学活动所应遵守的基本规则。但是即使牛顿也有赖于他的前辈,尤其是伽利略和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在这种意义上,他的贡献自然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假如牛顿从未来到过这个世界,科学的进展可能会滞后几十年。但也只是几十年而已。哈雷(Edmond Halley)或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也许会完美地提出著名的引力平方反比定律;就实际情况而言,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的确与牛顿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而且做得更好);而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颇具优势的光的波动说则因为牛顿对作为竞争理论的粒子说的支持而被阻碍了发展。
这都不能阻止我根据包括牛顿在内的这些人物,以我的叙事方式讲述科学史。为了突出这一思路,我在人物的选择上不求广泛全面,而我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与工作的讨论也不求完整。我选择了代表其所处背景中的科学进展的历史事件。其中一些历史事件以及所涉及的人物可能人们耳熟能详,其他(我希望讲到)的人和事大家则不太熟悉。但是这些人物及其生活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反映了其所生活的社会,并且通过讨论——比方说——特定科学家的工作方式与其他科学家之间的渊源,我意在说明一代科学家对下一代科学家产生影响的方式。这看起来可能像是以未经证明的假定作为论据,来回避球在最初时是如何滚动起来的问题,即原动力问题。但在这一个案中,很容易找到原动力——西方科学得以创立,是因为文艺复兴的发生。一旦科学得以创立,通过赋予技术以推进力,它确保了自己能一直保持平衡前行。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科学理论构想导致了技术的改进,而改进的技术则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以越来越高的精确性来检验新理论构想的手段。技术先行一步,因为在未能充分理解机器借以运行的原理时,通过试错来制造它是行得通的。但是,一旦科学与技术双剑合璧,发展就会突飞猛进。
我将把文艺复兴为何在彼时彼地发生的争论留给历史学家去解决。如果你想要一个确切的年代作为西欧复苏的开端的标志,一个信手可得的年份是1453年,也就是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5月29日)之年。到那时为止,很多讲希腊语的学者在察觉到风向后都已经向西(最初是意大利)逃去,并将他们的文献档案带在身边。对这些文献的研究由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运动接了过去继续开展,后者乐于利用古典著作中找到的教义,沿着黑暗时代之前已存在的路线重建文明。这的确将近代欧洲的崛起与古老的罗马帝国最后那点文明遗迹的毁灭相当巧妙地衔接到了一起。但是正像很多人曾提出过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14世纪因黑死病导致的欧洲人口减少使得劳动力变得非常昂贵,并激励了科技装置的发明以取代人力,而黑死病的发生也促使幸存者们对社会的整个基础产生了质疑。甚至这也并非故事的全部。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在15世纪中叶发展的活字印刷术对将会成为科学的那些东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由另一项技术进展——远洋船只——带回给欧洲的发现则改变了社会。
划定文艺复兴结束的年代并不比划定它开始的年代更容易——你可以说它仍在继续。一个信手可用的约略整数年是1700年,但是从目前的观点来看,一个更为合适的选择可能是1687年,也就是牛顿出版他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的这一年,用蒲柏(Alexander Pope) *的话来说,这是“一切尽皆光明”的年份。
我想要说的是,科学革命并不是孤立发生的,也肯定不是作为变革的主要动力而启动的,尽管科学在很多方面(通过它对技术以及对我们的世界观的影响)成为西方文明的驱动力。我希望表明科学是如何发展的,但与大多数充分呈现科学历程的历史书相比,我并没有花更多篇幅来将完整的历史背景充分展现出来。我甚至没有花篇幅把这里讲述的所有的科学充分展开,因此如果你想要的是诸如量子理论、自然选择进化论或板块构造论这样的关键概念的深入故事,你就得去看其他的图书(包括我自己的)。我对要突出强调的事件的选择必定是不完整的,而且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主观色彩,但我的目标是对约450年间的科学做出一个完整的快速扫视,这会带着我们从我们认识到地球并不是宇宙中心而人类“仅是”动物,一直走到大爆炸理论以及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图谱。
在《最新科学指南》(New Guide to Science,它和我可能曾希望写出的任何东西都截然不同)中,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说,向非科学家试图解释科学之历程的原因在于:
身处现代世界,除非对科学的历程有所了解,否则没有人能够真正感觉轻松自如并对问题的性质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做出判断。而且,对宏伟的科学世界有初步的了解会带来巨大的审美上的满足感,使年轻人受到鼓舞,满足求知的欲望,并对人类心智的惊人潜力与成就有更深的理解与欣赏。 *
我自己不可能说得比这更好了。科学是人类心智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否是“最”伟大的成就则尚存争议),而且,科学的进展很大部分实际上是由智力平平的人基于其前辈们的工作一步步推进的,这一事实让科学的故事更加不同寻常,而非相反。几乎任何一位本书的读者,如果在合适的时间身处合适的地点,都可能做出书中记述的伟大发现。既然科学的发展决不会停步,那么你们中的一些人也可能会参与到这个故事的下一个阶段。
约翰·格里宾
2001年6月
001 — 致谢
003 — 导言
001 — 第一篇 走出黑暗时期
003 —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
032 — 第二章 最后的神秘主义者
068 — 第三章 最早一批科学家
107 — 第二篇 科学的奠基人
109 — 第四章 科学立住脚跟
149 — 第五章 “牛顿革命”
192 — 第六章 拓展中的视野
239 — 第三篇 启蒙运动
241 — 第七章 理性启蒙的科学Ⅰ:化学迎头赶上
284 — 第八章 理性启蒙的科学Ⅱ:各个领域的进展
315 — 第四篇 大图景
317 — 第九章 “达尔文革命”
358 — 第十章 原子与分子
399 — 第十一章 要有光
441 — 第十二章 经典科学的最后欢呼
485 — 第五篇 现代
487 — 第十三章 原子之内
529 — 第十四章 生命领域
572 — 第十五章 外层空间
613 — 结语 发现之乐
619 — 译后记
622 — 参考文献